離岸+金融只是逃稅、洗錢的代名詞?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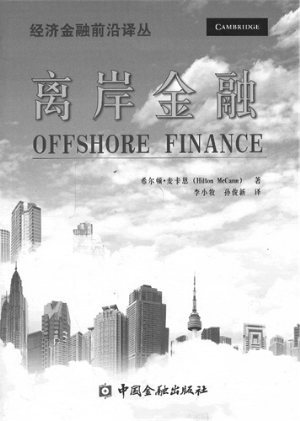
《離岸金融》
(美)希爾頓·麥卡恩(Hilton McCann)著
李小牧 孫俊新 譯
中國金融出版社2013年6月出版
—— 評希爾頓·麥卡恩《離岸金融》
據說在任何一種語言中,“離岸”(offshore)一詞只要和金融共同出現,往往會透露出些許“邪惡因子”,并會挑起某些“緊張情緒”,因為這個組合詞總被理解成為“逃稅”、“洗錢”等犯罪行為的代名詞。更容易引發緊張的理由是,所有的私人銀行都會跟“離岸金融”扯上關系。但離岸金融中心的作用卻萬不可低估。據有關機構估計,早在20世紀90年代初,世界貨幣存量的50%通過離岸市場周轉,世界五分之一多的銀行資金、約有五分之一的私人財富都投資并集中在離岸市場上。
曾在馬恩島、馬耳他和毛里求斯等從事銀行監管工作多年的美國知名經濟學家希爾頓·麥卡恩(Hilton McCann)在《離岸金融》中,試圖以“過去”(20世紀30年代至90年代末)、“現在”和“未來”三個明確的時間層次為引子,去打通服務、稅收、監管、保密等的通道,以探尋并審視離岸金融80余年充滿“爭議”的嬗變歷程和奧秘。即使其個別觀點值得商榷,有的論據還需推敲,但通讀該書,筆者認為仍有益于激發思考,開啟智慧,有助于我們對離岸金融相關問題的深入研究與探索。
離岸金融中心,是指以自由兌換貨幣為交易媒介,非居民參與為主,提供借貸、結算、資本流動、保險、信托和證券、期貨、衍生工具交易等金融服務,且不受市場所在國和貨幣發行國一般金融法規和法律限制的金融中心。由此,離岸業務的特點是信用證申請人和受益人都在境外。通俗地說,就是“兩頭在外”:從事離岸業務的機構從境外吸收存款——債權在外;向境外發放貸款——債務也在外。當下,國際上的離岸金融市場大致有三種類型:兼具境內和離岸業務的“內外混合式”的倫敦型市場;境內與離岸業務“內外分離”的紐約型市場;設在巴哈馬、百慕大群島、開曼群島等以避稅為目的的“避稅港型”的離岸市場。
在麥卡恩看來,離岸金融市場的產生與戰后各國經濟、資本國際化和貨幣領域里的政策變革密切相關。認識離岸金融,麥卡恩提醒人們不要忘記對“三個利益團體”的關注:其一,離岸金融中心本身,它是“賣方”和“買方”交易的市場。其二,“賣方”或者說服務的提供者,也就是那些向最終消費者提供金融服務的商業機構。范圍可以從大型銀行到小型信托機構,以及合資服務公司。其三,就是“買方”——服務的最終消費者,比如“離岸”信托機構的那些建立者。此外,麥卡恩還發現,針對“保密性、稅收和監管是引發對離岸金融中心環境最多爭議的原因。”
先說說“保密性”和“稅收”。如果甲某覺得個人信息在本國容易暴露的話,他可能會通過在提供保密制的外部區域投資。一般來說,為了增強“保密”,存款者/投資者往往將資產從母國(應納稅國)轉移并且將資產存儲在離岸金融區或是以儲蓄計劃(比如保險、養老金、集體投資計劃等)在離岸金融區投資。傳統上,法國人利用瑞士,德國人利用盧森堡,而余下的大部分都是利用倫敦和美國(因為其在建立信托機構和離岸金融公司以吸納資金和避免雙重征稅上擁有先進和成熟的方法)。在儲蓄到期(或資產贖回)時,其資金及所有收入一切回饋給所有者。在資產所有者的母國,資產所有者有義務申報收入,但由于東道國(離岸金融中心)稅務當局不會向資產所有者的母國稅務當局報告該筆收入,除非母國居民自行申報。更為可能的情況是,母國的法律要求他公開其收入。盡管在法律上納稅人有義務公開,但大多數納稅人并不會將公開看作道德義務。在此基礎下,唯一的損失者就是母國政府——因而母國政府反對漏稅最為強烈。
“在這世界上,只有死亡和稅收是不可避免的。”不過,對于那些富有并精明的人而言,恐怕只有死神才是真正擺脫不了的。因為,富豪們的私人銀行會想方設法通過規劃交易來幫他們大幅度減少稅單,有時則可以使一些稅務完全消失。
所以,將資金放在離岸基金上避稅,一直是私人銀行家們樂此不疲的招數。
麥卡恩在對比研究中發現,離岸金融的“吸引力”不僅局限在個人。一些跨國公司在開展國際業務時,如果使用離岸金融區服務便可規避一些賦稅。離岸金融中心最具吸引力的地方在于稅收優惠、寬松的政策及其他諸如保密之類的特殊規定。離岸金融中心的注冊費用和維持成本低廉,在維爾京群島,非居民只需就來自本地的收入納稅,沒有資本利得稅,注冊公司享受包括預提稅在內的稅收豁免。另外,很多離岸中心都與主要經濟大國簽署了避免雙重征稅條約。
離岸金融業與傳統銀行業務相比具有很大優勢,在世界各地離岸金融中心的銀行可免交存款準備金、稅收又有不同程度的優惠,這使離岸銀行業務的經營成本明顯低于在岸業務。經濟的全球化與離岸金融關系十分密切。貿易逆差國往往對本國進口商和外國出口商融資有諸多限制,因此國際貿易商就產生了能不受限制地獲得低成本融資的需求。與此同時,有閑置資金的國際貿易商則期望能有個存取自由、利率相對較高的金融場所,離岸金融市場就成為不錯的選擇。當然,跨國公司在國際金融市場籌措資金時常還會有一些特殊要求,比如保密和避稅。加勒比海等地區的離岸金融中心正是因此而繁榮。1974至1980年間,美國公司包括通用汽車這樣的大跨國公司的分支機構,用上述方式共舉借180億美元的歐洲貨幣債務。
這樣一來,離岸金融環境確實有強大的吸引力,而對當地政府而言,離岸金融業務則意味著財政收入。大量跨國銀行和企業的到來,不但為國家帶來了豐厚收入,還解決了當地居民的就業。因此政府竭盡所能通過政策維持這種優勢。比如有“避稅天堂”之稱的開曼群島,是世界第五大離岸金融中心,其政府能隨時修訂法律,以保持其在金融、保險、商業等方面的領導地位。跨國公司利用避稅地避稅,無疑會損害高稅國的稅收利益,所以高稅國對本國公司向境外轉移資金十分關注。而開曼群島在1966年就頒布了《銀行和信托公司管理法》,規定了為客戶保密的原則。1976年又制定了《保密關系法》,由于有嚴格的保密法,外國政府很難從開曼的銀行取得客戶存款賬戶的信息。
提到“監管”,麥卡恩認為“預防通常會比治療好”,監管過程會受到各種各樣的因素影響——但是也許人性因素是最易變和最難預測的一方面。當業務水平下降、部分被許可人轉移到國外時,引用“過度監管”作為原因,權威人士就必須重新考慮他們的監管方法。需要指出的是“離岸金融的標準正在變化,最初的時候規則很少,所以第一步只是引入一般規則,接下來便有了特別規定,再后來就有了遵守控制和更高透明度的要求。最新的發展便是對信息披露與信息交換要求的鞏固。”
在過去的20多年里,離岸金融中心一直是大國、富國之間的博弈焦點。全球外商投資中,30%借道離岸金融中心。離岸金融中心能成為避稅地,而長期以來歐美國家聽任其存在,這本身就是大國角逐的結果。即便到了今天,歐美國家對離岸金融中心的討伐仍然是三心二意,欲說還休。
赫赫有名的“稅務計劃人”杰羅姆·施耐德(Jerome Schneider)首先提出了偷稅漏稅的諸多方案,公然將其刊載在雜志上。全球范圍內的50~60處避稅港是超過200萬家空殼公司、數千家銀行、基金會和保險公司支付期票的場所,全世界載荷量超過100公噸的注冊船只中,也有至少半數在此交易。避稅港里的交易額度無人知曉,而那屬于非法收入的部分也便就無據可查了。實際上,離岸金融市場作為“完全國際化了”的國際金融市場,與近年來無處不在的“熱錢”有著千絲萬縷的關系。
英國金融服務局前主席霍華德·戴維斯曾說:“除非離岸金融中心的反洗錢監管能夠得到改進,否則離岸金融中心將面臨一個"暗淡的未來"。”與戴維斯的悲觀看法迥然不同,麥卡恩對離岸金融卻抱有很高的期待和期望:“未來"離岸"和"在岸"的區分不會集中在地理位置和概念理解上,而是具體在金融服務中心如何才能被監管。也就是說,監管本身并不重要——重要的是監管在多大深度上被認為是聲譽的主要組成部分,而聲譽是衡量安全與否的標準,對投資者是否愿意與特定的金融中心進行生意往來具有決定性作用”;“未來,籠罩著離岸金融環境多年的神秘面紗將會被揭開,離岸金融會實現前所未有的透明化,離岸金融中心不會被用于沒有透明化的交易。”
理想是否過于完美、藥方是否過于簡單,目前或許只能拭目以待。但麥卡恩似乎也把更精彩的離岸金融故事,寄托給了長遠的未來。

